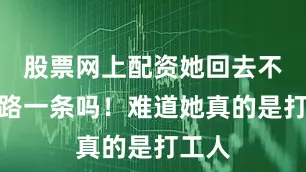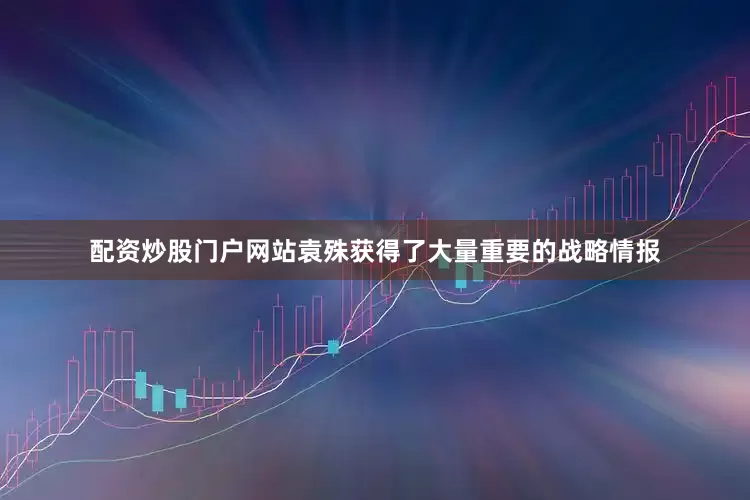
中共情报史上有许多传奇,号称“五重间谍”的袁殊就是其中之一。
袁殊,原名袁学易,出生于湖北蕲春,1925年改名袁殊,1928年赴日留学,1931年3月在沪创办并主编《文艺新闻》周刊,最早发表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,1931年10月经潘汉年介绍秘密入党,开始从事情报工作。

△袁殊
他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,广泛交际,先后结识中统要员吴醒亚、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等人,获取了大量情报。后来,袁殊与特科的联系一度中断,其组织关系转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。
1936年5月后,袁殊去日本留学。袁殊到日本后,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给他提供了许多帮助,不仅为他解决了留学期间的费用,还介绍了一些日本政界和学界人物和他认识。
岩井之所以特别关照袁殊,当然不是所谓的朋友之谊,而是培养袁殊亲日,拉拢他为日方效力。1937年4月,袁殊从日本回国,暂居青帮头子杜月笙的门下。

△袁殊(后排右一)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同学的合影
不久,全面抗战爆发,军统急于开展对日的情报工作,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。
戴笠得知袁殊两度留学日本,又与日本领事馆关系密切,亲自找到袁殊,要他加入军统抗日。袁殊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。
1937年11月12日,上海沦陷。潘汉年撤往香港,行前向袁殊交代: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,但有关情报事务只与他本人单线联络。
1938年2月,岩井英一回到上海任驻上海总领馆副领事。4月,岩井成立了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——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,又称“岩井机关”。

△日本领事馆
岩井知道袁殊背后复杂的关系,希望袁殊为自己工作。袁殊也想利用此机会获取日方情报,便欣然同意。
在岩井公馆,袁殊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战略情报,包括: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“远东慕尼黑阴谋”、日本外务省决定同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、日本少壮派白岛敏夫等人同苏联驻日外交人员的秘密接触情况等。
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决定南进的战略计划。
在日本外务省的安排下,袁殊应邀访日,受到日本天皇和首相的接见,并与各级政要会谈,期间日本外交官野村吉三郎曾向袁殊透露,日本政府已确定了放弃北进、实行南进的重大战略决策。
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震撼,回国后他立即报告潘汉年,中共中央随即密告苏联政府。

△潘汉年
从1941年开始,袁殊又打入了汪伪政权。自此,袁殊已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、国民党中统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、国民党军统、汪伪政权,因此,很多文章称之为“五重间谍”。
但实际上,只有中共对其各种身份都掌握,袁殊真正忠诚的还是最早加入的中国共产党,他始终都是中共的谍报人员。
那么,情报史上有没有真正的双重间谍?
当然有。孙子在其兵法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
孙子非常重视反间,认为反间是五间的枢纽,“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,因而利之,导而舍之,故反间可得而用也……五间之事,主必知之,知之必在于反间,故反间不可不厚也。”

△孙子画像
杜牧认为,“乡间、内间、死间、生间,四间者,皆因反间知敌情而能用之,故反间最切”。
黄朴民认为,“这个关键,就是在‘五间’之中要以‘反间’为主,带动其他的‘四间’,广开情报来源,动员各种类型的间谍,运用各种手段窃取敌人的情报……从而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”。
这些解读深刻揭示了“反间”在谍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。
一个敌方间谍如何才能成为“反间”?
孙子指出,“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,因而利之,导而舍之,故反间可得而用也。”历代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尽相同,争议的焦点集中于“导而舍之”。
曹操认为“舍,居止也”,杜牧也说“敌间之来,必诱以厚利,而止舍之,使为我反间也”。但明代赵本学给出了不同的注解:“因而厚利以诱其心,导之以伪言伪事,而纵遣之。”将“舍”解释为“纵遣之”。

△明代赵本学注本《孙子兵法》
两种说法,当以赵注本为上。
确定一个有多重身份的间谍是否为双重间谍,主要看两点,其一是他是敌间,其二是他被我逆用,舍此则不能断定其为双重间谍。如袁殊,不管他有多少身份,他也只是中共的情报人员,而其他的身份都是他的掩护色。
在国际谍报界,英国军情五局和苏联克格勃,都是反间的高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控制了全部德国间谍,并通过他们传递假情报。

△英国军情五局正门
军情五局负责经营双重间谍体系的约翰·马斯特曼总结了双重间谍的七个作用:
(1)控制敌方的谍报系统;(2)捕获新渗透进来的间谍;(3)获取敌方谍报机构的情报;(4)获取敌方的无线电密码和破译密码所需的材料;(5)探索敌人的意图;(6)通过传递假情报来影响和改变敌人的计划;(7)对敌人实施欺骗。
苏联情报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控制了德军的全部间谍,并渗透了英国军情五局、军情六局等关键情报机构。他们在维护国家安全、了解对手的核心机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杠杆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